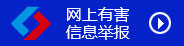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每年春天舉辦“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首先我代表體改研究會,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在百忙之中參加這次會議。都說政府官員在百忙之中,現在許多學者比官員還忙。對于學者來說,總處在百忙之中是好事還是壞事,值得研究。雖然參加座談會的人員不多,但是歷年來“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上所碰撞的思想火花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雖然座談會規模不大,但是參加的學者多是國內頂尖的,討論的內容涉及當前經濟社會面臨的重大、關鍵問題。
今年的座談會重點放到哪里?從近期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所謂“后危機時代”的政策選擇。我國率先擺脫了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各項經濟指標向好,GDP總量要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那么刺激政策應當及時退出,還是繼續保持連續性、穩定性?世界經濟、中國經濟會不會二次探底?在應對危機中,政府采取措施的積極成果是什么,有哪些后遺癥?人們還有不同看法。從學者的爭議看,有人說這次危機證明政府應該加大對金融的監管、加大對市場的干預;有人說這次危機恰恰證明應該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應當堅決摒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還有人論證這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崩潰的前奏。
從中期看,“十一五”規劃今年結束,“十二五”規劃正在醞釀出臺,這涉及5年的工作安排。怎樣評價“十一五”規劃的執行情況,如何確定“十二五”時期的工作重點,特別是“十二五”時期的改革重點,學者中間也有不同的意見。中央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但如何落實還是一個大問題。一些省市提出要以加快發展速度來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有的提出要充分發揮投資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引領作用,就連我國外貿依存度是否過高、居民消費率是否過低,都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從長期看,前年紀念改革30周年,去年慶祝建國60周年,站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很多人在探討改革下一步怎么走?中華人民共和國下一步怎么走?這方面社會各種思潮起伏,存在的爭議更大。究竟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還是問題已經上升為主要的?我們不能否認30年來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極大的提高,我們也很難否認這30年來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不斷積累,有的已經很尖銳。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是繼續深化改革,還是退回計劃經濟?胡錦濤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的成績不容否定,要堅持改革不動搖,停頓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時候召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我們建議這次會議的重點放在中近期的改革研究上,討論一下“十二五”時期到2020年期間我國面臨的經濟社會形勢以及在這一背景下應當重點推進哪些領域的改革。
大家知道,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判斷,認為在2000年左右,也就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初步構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框架。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并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從框架初步構筑到體系比較完善,中央預計要20年左右。現在我們正處在這20年的中點。國家發改委領導給體改研究會出了個題目,要我們研究一下前10年改革取得了哪些進展,目前還有哪些問題,到202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重點推進哪些方面的改革,這一時期改革的主線是什么,有關各項改革的次序如何確定。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如何入手,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體改研究會常務理事會就這一課題討論過一次,又征求了一些學者的意見,多數人認為“十二五”至2020年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改善民生為目的、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來推進改革。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推進改革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說應當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來研究改革,而不是事先預定一個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按這個理論體系的要求來衡量改革;二是說要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深化改革,沒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綜合配套改革,發展方式的轉變就難以落實。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很多,如內需與外需失衡、投資與消費失衡、城市與農村失衡、勞動與資本失衡、壟斷與競爭失衡等,其中政府與市場失衡可能是諸多失衡的連接點。衡量失衡的指標很多,能不能在眾多的指標中找出一兩個關鍵的指標,這一兩個關鍵指標可以把其他的指標涵蓋進去,帶動起來,這樣主線比較清楚,邏輯比較嚴密。一些學者提出,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是否可以把提高消費率列為關鍵指標來展開研究。提高消費率,不僅涉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內貿與外貿的比例,還涉及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同時與促進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密切相關。能不能提出到2020年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從目前的35%左右提高到45%或更高一點,比如50%左右?這要根據我們到2020年的人均GDP與世界其他國家在這一發展階段的居民消費平均水平來確定。居民消費率的指標大致確定后,就可以進一步分析要實現這一目標,城市化進程指標、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指標、投資比重的指標、內需的指標等需要做哪些相應的調整。然后再分析如果要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勞動報酬比例、適度壓低過高的投資比重等,需要在財稅體制、外貿體制、金融體制、就業體制、分配體制、社保體制以及戶籍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哪些改革,這些改革是否需要政府加大職能轉變的力度,特別是要厘清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2010年提出的GDP增長速度平均為10.3%,比中央提出的8%預期目標高出30%。地方人大通過的GDP增長指標實際是指令性的,對各地市執行情況要年中檢查,年底排隊。各省市、各地市環顧左右,沒有一個愿意在GDP增長上落后的。這樣,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真正落實恐怕要大打折扣。計劃經濟時政企不分,把企業搞成政府的附屬物,企業也是一級行政機構,科級、處級、局級、部級。現在新的政企不分是把政府搞成企業,鄉鎮政府領導有的就是當地工農商企業總經理。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進一步改革財稅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和干部考核任免制度不行。
因此有的學者提出,如果以某一指標的落實來設計改革,圍繞一套指標體系來設計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再把指標分解落實到各級政府,其結果可能南轅北轍,搞成計劃體系了。有的學者指出,面對當前諸多社會矛盾,是靠構建一個更精致的政府來解決?還是靠培育社會自調節機制來解決?我看兩方面的問題都有。我認為,從實際問題出發來研究改革,并不排除從理論上研究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明確問題所在,還要明確解決問題所遵循的原則與路徑,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舉個例子,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可以數量化的,比如從現在的11%左右提高到20%左右。問題在于通過何種途徑實現這一目標?是使用行政手段還是發揮市場機制來提高這一比例?用行政的辦法也可能在一段時間較快奏效,強令企業給職工漲工資,制定工資倍增計劃,而我們如果搞工資倍增計劃與日本當年的可不一樣,很可能要層層落實到各級政府一把手責任制。但這是否不適當地干預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靠政府運作也可能把工資提起來,可是從長遠看,這是在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還是在走回頭路?
今年“兩會”期間我在政協全體會議上發言,講到目前一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所占比重過低。會后有學者說,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勞動報酬低是市場供求規律決定的,政府怎么能干預一次分配呢?似乎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對于一次分配,政府是否就無作為了呢?分析一下不難發現,現在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們沒有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的結果,許多政策對一次分配造成了負面影響。
首先,農民工工資長期偏低,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歷史形成的戶籍制度割裂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工人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有學者估算過,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三、五千億元,比減免農業稅多得多,更不用說家電下鄉的補貼了。這筆賬多年累積下來,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影響有多大?戶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積極穩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政府責任重大。
其次,一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如果把證券業歸到金融業一并計算,行業差距也高達6倍。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后期,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只是制造業的1.38倍。這些國家金融行業的高工資并不是由其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業對知識的要求比較高,從業者受教育年限較長,付出成本較高,因而要求的回報也相應較高。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力自由、合理流動,行業工資差距其實是各個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從目前的資料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已經超過巴西。如此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嗎?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再深入分析還有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等問題。合理調整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以及推進與此相關的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當然是政府的責任。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在較長時間內重視招商引資,也有意無意地壓低了勞動力成本。
最后,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一般勞動力價格會被壓低,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中的工資水平不僅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還要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關鍵問題是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正如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工會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所指出的,企業工會干部大多數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情況造成工會干部很難真正代表職工的利益。我認為,工會組織為勞動者維權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是我國勞動報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原因。
可見,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但主要不是依靠層層落實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為,而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上下功夫,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類似的問題很多,關鍵在于解決問題的途徑是進一步推進改革還是退回去搞指令性計劃管理。
對于下一步改革如何深化,現在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有點兩軍對壘,劍拔弩張的感覺。前天我參加一個課題研討會,一位地方廳局長說:原來中央一聲號令,各地朝一個方向跑,類似奧運會;后來各地發展很不平衡,但中央一聲號令,不管腿瘸腳歪快跑慢走,總還是朝著一個方向,類似殘奧會;現在對經濟社會問題各方面認識大相徑庭,一聲槍響,往前后左右跑的都有,還有的蹲在原地問剛才哪里爆炸了?類似特奧會。特奧會是智障者運動會。我記得列寧說過,比喻都有蹩腳之處,這個比喻也不是那么貼切,但還是值得學者們深思。希望我們這次座談會開成奧運會,至少開成殘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