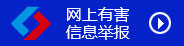宋曉梧,曾在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國家發改委擔任要職,對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問題有深入觀察。他認為,解決職工安置問題,中國應當推行一系列積極的就業政策,借力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剝離國企辦社會的職能來減少壓力,同時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
《財經》記者 相惠蓮/文
在職工安置上,資金應該怎么花,花到什么地方?如何促進分流、轉崗人員的再就業?
帶著這些問題,《財經》記者專訪了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他曾在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國家發改委擔任要職,對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問題有深入觀察。
宋曉梧提出,解決職工安置問題,中國應當推行一系列積極的就業政策,借力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剝離國企辦社會的職能來減少壓力,同時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
中國的特殊問題
《財經》:職工安置是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在您看來,目前中國去產能面臨著怎樣的局面?
宋曉梧:經濟進入新常態,去產能是當前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都與去產能密切聯系在一起。
實際上,過剩產能有幾種類型,共存、交織于當下的中國。
第一種是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產能過剩。一個國家的鐵路、公路、高樓、住房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進入平臺期,再上升就很慢了。在高速上升階段形成的鋼鐵、水泥、煤炭、焦炭等產能到了轉折時期,就顯得過剩了,這也是發達國家都經歷過的。
第二種是可能市場還有一定容量,但環境不允許再存在的產能。例如一些鋼鐵、水泥、煤炭企業,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造成的生態污染社會難以承受。要達到新的嚴格的環境排放標準,這些企業的產能不得不被淘汰。
第三種是從工業化以來一直不斷出現的投資與消費不平衡造成的產能過剩。
由于分配不公平,普通生產者收入不夠高,不能充分消費快速增長的產能制造的產品。
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盡管有一部分人到國外消費,但是有多少農民工、普通工人、農村人能夠做到?13億人口中,有2.7億農民工,至少6000萬留守子女,5000萬到6000萬留守老人,將近3000萬留守婦女,大約5億人,沒有多少消費水平。還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更沒有多少消費能力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前階段有大量產品可以輸出,成為世界加工廠,但一旦世界經濟緊縮,這種過剩就更加凸顯。
《財經》:這幾種產能過剩是海內外都有過的,對中國來說,是否面臨著一些獨特的情況?
宋曉梧:這三種產能過剩發達國家在各自的發展階段都經歷過。
如果說與其他國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國政府干預市場的能力要比它們大得多。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地方官員為了自己在執政期間三到五年內的政績,過分追求GDP增長,以壓低地價、讓利讓稅、壓低勞動力價格、犧牲生態環境等手段招商引資。政府間的互相競爭大大加劇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難免形成的產能過剩,很多產業一哄而起。
典型的例子是清潔能源,雖然有很大潛力,但任何發展都要與其他條件匹配,風電、光伏等發展都需要與電網輸送能力相匹配。前幾年600多個城市中300多個提出要把光伏、風電設備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就像前些年紛紛提出把汽車、鋼鐵、水泥等作為支柱產業那樣。
地方政府公司化競爭,極大地加劇了產能過剩,這是中國的特點。上世紀80年代改革剛起步時我們就申明堅決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現在中國的污染更為嚴重。
我在2004年就寫文章提出要防止政府政績沖動與企業利潤沖動相合流造成經濟過熱、產能過剩。遺憾的是這種情況沒有得到制止,過去十年之中反而越來越嚴重。這是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特殊背景。
《財經》:地方政府過度競爭的問題應當如何解決?
宋曉梧: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多措施,最重要的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堅持認為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指標應當淡化直至淡出,況且GDP指標本身就不是用來考核一個市縣的。
很多人已經認識到,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單純的、周期性的產能過剩,而是發展階段性的、生態約束性的、分配失衡性的產能過剩。因此,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應該以嚴格的環境標準來限制企業,凡達不到環保標準要求的,不論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一視同仁加以限制。同時,還需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共享發展,讓社會財富分配得更均衡一些。
《財經》:在去產能、安置職工的過程中,中國的國企和民營企業是否面臨著不一樣的局面?
宋曉梧:對國有企業而言,辭退職工更難一些。降低國有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首要的辦法是剝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
企業辦社會的問題在東南沿海地區基本解決了,但在老工業地區,包括東北、西部和內地許多地方,企業辦社會的問題仍大量存在,有的整個城市就是在油田、煤礦或林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經濟效益一旦下滑,這類問題尤其突出。
參與企業辦社會的就業人員相當多。當企業經營處于上行期時,這些人力成本在總成本中被攤薄了,不明顯,在企業的總利潤下滑、虧損的情況下,這部分人力成本就會凸顯出來。
例如,東北有的企業產能利用率在2010年為110%,工人加班加點,超負荷生產,2015年產能利用率降到50%以下。訂單減少,能源、原材料等流動成本大幅下降,而工資成本卻難以同步下降,因而勞動力成本占比大幅上升。
一家民營企業在2010年時人工成本只占總成本的15%,現在已占到將近40%,工資成本占比大幅上升了2-3倍。只看這個數字會以為近年來工資提高太快了,實際上工資總額還減少了將近50%。勞動力成本占比提高的真實原因是生產總成本減少了80%。
因此,對過剩產能行業而言,不是工資增長過快造成勞動力成本占比上升,而是總成本下降幅度遠大于工資下降幅度,由此造成勞動力成本占比上升。
在這當中,相當一部分勞動力成本是企業辦社會的成本。例如對企業辦的學校、醫院來說,無論企業的效益好壞,教師、醫生護士的工資福利都不可能大幅度減少。這種情況是國有企業去產能過程中面臨的特殊問題。應該借著這輪去產能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下大力氣解決企業辦社會的問題。其實,這部分人員比較容易解決,醫院、學校對企業來說是沉重負擔,對全社會來說是緊缺資源,理順企地關系,搞好了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推行積極就業政策
《財經》:對于本次的職工安置,中國過去是否有一些經驗可以參考?
宋曉梧:東北、山西、河北是三個全國產能過剩最嚴重的地區,集中在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炭、裝備制造等行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大幅度地提高技術標準,錢從何來?另外,明確削減產能后,人員怎么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
從實際操作看,中國在1998年之后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下崗分流,涉及三四千萬國有企業職工。當時,先在企業內部成立職工再就業中心,經過一段時間,逐步分流到社會上去,同時加強轉崗培訓,提供公益崗位,幫助零就業家庭,為自謀職業者提供支持等,這是中國自己的經驗。
《財經》:產能過剩并非中國特有,國外在這方面是如何處理的?
宋曉梧:全世界范圍內都會發生這三種情況的產能過剩,有些解決問題的措施值得我們借鑒。比如德國的魯爾區,煤挖光了,工人怎么安排?還有法國的蘭斯、北加萊地區的煤礦,英國、美國、日本都有過類似的案例。
這類資源枯竭性產能過剩,在我國目前又凸顯出來,國務院在2007年出臺過解決這一問題的指導意見,近期又出臺了相關規劃,其中許多措施是借鑒了發達國家經驗的。
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這些國家都對特別衰退行業職工的安置問題執行特別法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鋼鐵業經過一段高速增長后面臨產能過剩,一些加工業也面臨著產業轉移,為此日本曾經出臺過特別衰退產業退職人員安置法,推出了很多具體措施,如對轉業人員領取失業金的期限做特殊照顧,雖然當時網絡還不發達,但仍然想辦法提供公共就業信息,對于招收特別蕭條行業退職職工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補助,等等。
我認為,對于職工安置最主要的措施是對職工進行轉業培訓,培訓期間給予補貼,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對雇傭這些人員的企業提供稅收鼓勵,對自謀職業者給與稅費減免;對有一定經營能力和特殊技能的創業者,給與創業擔保貸款和場地安排等政策扶持。此外,對一些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員,可以實行內部退養,由失業保險基金給予合理支持。
《財經》:中國安置職工的難點在哪兒?
宋曉梧:企業辦社會的部分,如醫院、學校、消防隊,甚至市內交通,剝離出去比較容易,能大大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負擔。當然,這其中的冗員也應當借助這次剝離的機會加以壓縮。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不再需要那么多一線的產業工人,這和西方國家一樣。但在西方國家,失業率在經濟蕭條時期會大幅上升。比如美國,在次貸危機后,失業率迅速從6%左右上升至12%左右,經濟好轉時慢慢降到10%,徘徊了很長時間后又降下來,現在已基本恢復了正常。
西方為什么是這樣的情況?因為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比較好,很少有國有企業。
對美國而言,在過去幾十年里,GDP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基本是吻合的。美國為什么會是這樣?工資是有剛性的,經濟蕭條時能降低工人的工資嗎?其實,這背后不是降低工資,而是裁員。
但在中國,經濟增長率與工資增長率兩者的變動趨勢差異很大,經濟增長了工資不一定增長,工資增長了經濟未必增長。說明我們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差。
民營經濟的靈活性較高,解決民營企業職工安置問題相對容易,但國有企業很困難,還要講求穩妥。在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剝離之后,就要裁減其中企業一線不再需要的人員,大量勞務派遣工和農民工的安置相對容易。對于管理、技術等核心人員,企業應該根據將來的發展和市場行情來考慮。
美國企業在困難時期也不是都解雇,而是保留核心人員,一旦生產形勢好轉,招人就能開工。除非是企業徹底破產,那就按破產程序來解決,第一利益保護人就是職工,按照破產程序進行安排。
《財經》:對職工利益的保護,可以有哪些作為?
宋曉梧:在這方面要政府加強監管力度,另外,國有企業還有一定社會責任。需要注意一個問題,不管是哪個國家,在經濟下滑時期,政府的注意力都是更加關注弱者,關注失業群體和職工的安置。當然要創造條件讓企業發展,要平衡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兩者關系,但著力點應當放在保護普通勞動者方面。
羅斯福新政時期,面臨經濟大蕭條、企業大量倒閉的局面,第一件做的事情是通過勞動法、最低工資法、社會保障法,這些重大社會政策都是側重保護工人的利益。現在一些學者總結羅斯福新政,片面渲染政府加大投資的經濟政策,對他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避而不談,我認為有所偏頗。
《財經》:您提到在解決職工再就業時要加大培訓力度,這將會怎么做?對于企業內不同的人群是否會做不同的處理?
宋曉梧:我們在這方面有經驗。轉業培訓對于二三十歲、三四十歲的人員比較好辦,這些人的學歷也相對高。德國的煤炭企業關閉以后,他們把工人安置作為頭一項重點任務,培訓很多年輕人向電子等新興行業發展。對年紀大的職工,給予寬松政策,允許他們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會對養老金和財政造成壓力,但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不可能這時候還展現高速發展的玫瑰色。轉型期難免要兩害取其輕,是選擇社會不穩定,還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把不該花的錢堅決省下來,把可花可不花的錢盡量省下來,節省開支補充社會保障?這需要壯士斷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財經》:失業保險目前面臨著結余多、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在這次職工安置中怎么發揮更好的作用?
宋曉梧:失業保險的錢花不掉,正好能在這次職工安置中發揮作用。第一,減輕企業負擔,可以適當降低一些企業的繳費率。第二,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大力度用失業保險金來支持再就業和專業培訓,另外,在公益崗位就業服務上對鋼鐵、煤炭員工給予特別的照顧。
促進勞動力市場統一
《財經》:在經濟下行的形勢下,是否存在就業壓力大的問題給職工安置帶來困難?
宋曉梧:有些人說“十三五”時期中國就業問題不大,理由是勞動力總供給壓力減輕,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減少兩三百萬,同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得差不多了。
我認為就業不單純是總量問題,還有結構問題,最突出的是農民工和大學生,還有今天談到的去產能問題。
人均GDP為兩三萬美元以上的國家,恰恰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之后,勞動糾紛、就業問題更加突出。農村勞動力還能大量轉移時,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時期。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產能過剩,解決不好職工安置問題就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勞資矛盾。日本、韓國,都是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致轉移后出現大規模的罷工事件。
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的就業群體,他們進城多年,又享受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和正式職工的待遇。2.7億農民工中,1億多是在當地轉移的,1.7億異地就業。這對社會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不穩定因素,也不合理。其他國家經歷工業化過程時,由于沒有戶籍制度帶來的城鄉行政隔絕,沒有產生過這樣的問題。在去產能過程中,對企業來說,農民工比較好解決,但對國家而言,如果農民工,尤其是回不去農村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出路,將是社會風險的集聚。
《財經》:一些城市發展和當地企業綁定得過緊,當企業發展效益不好時,本地提供的就業崗位是否存在不足,在安置職工時是否牽涉到異地安置?
宋曉梧:一些地區直到現在政企都沒有分開,它們的就業崗位確實存在不足,所以東北的人口大量轉移出來,以十年200萬的速度。
如果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異地就業、勞動力流動會是很正常的現象。美國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在一年之間會變換工作、會流動,工資變動情況和經濟增長變動情況吻合得那么好,說明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相當不錯,比歐洲還強一些。
《財經》:那么在促進勞動力流動、統一全國勞動力市場方面,有哪些能做的事情?
宋曉梧:影響勞動力流動的一大因素是社保難攜帶。
對于資源枯竭型地區、老工業地區,要解決職工的養老和社會保障問題,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安排,把基本社會保障的事權提到中央和地方共管,統一全國費率,實現全國范圍的共濟,達到區域平衡。
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是指一個地區的均等化,而一定是全國的。加拿大在立國時就明確,所有州的公民要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在教育、醫療、養老、基礎設施方面,發達地區要支持欠發達地區。美國是聯邦制,各州有相對的立法權,但美國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從1935年社會保障立法之日起,各州就是統一的。中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過分強調一地的GDP增長,多年來走不出這個誤區,造成了嚴重的區域差距問題。
應該盡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實行全國統一費率,實現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共濟。這種共濟是有道理的,比如大慶油田作為央企,主要稅收在中央,工人退休后在地方,黑龍江財政這么困難,還需要承擔起大量央企職工的養老,顯然是不公平的。實際上,大慶油田通過交稅也給發達地區帶去了紅利,廣東等地區享受了中央給的種種財政上的優惠政策,養老的負擔又比較輕。企業繳費率只有13%,而黑龍江長期是22%,近年才減到20%,結果收不抵支。因此,基本社會保障項目應該全國統籌起考慮,不宜各省各地自行決定。
不統一的養老保險政策會進一步擴大區域差距。有人問,為什么黑龍江自己的企業在發展起來以后要到別的地方投資,而不再到本地投資?
企業家的回答很簡單,在黑龍江投資一個招收1萬名工人的企業,1名工人平均每月5000元工資,一年的工資成本是6億元。在黑龍江繳納養老金的比例是22%,而在廣東只需繳納13%,兩者相差9%,即企業在廣東發展每年可以省下5400萬元,那我為什么要在黑龍江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