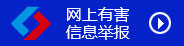“對加快實現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而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極其重要,其不僅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舉措,還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更是堅定政治信仰的群眾基礎。”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符合當前百年未有之國際國內局勢變動的客觀要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中,分配問題長期以來十分突出。這是經濟運行有效需求不足的重大成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經濟循環,同時也在社會層面造成階層分裂,應當作為進一步凝聚民心,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提到緊迫議事日程。
一、進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打破“大鍋飯”“鐵飯碗”,以先富帶后富的戰略,極大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居民收入的長期快速增長。同時形成了以國家立法實施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為基礎,以城鄉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大體保持同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為居民解除后顧之憂,這是促進國內消費,實現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礎性平臺。
在充分肯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國內經濟大循環提供了較好基礎的同時,也應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穩定居民預期,從而提高消費水平的空間還很大。目前,我國的總體消費率從2010年的48.1%逐步提高到2017年的53.4%,距2000年的63.9%還有較大差距。居民消費率從2010年的35.3%提高到2017年的38.8%,距2000年的47.2%也有很大差距。歐美及日韓等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說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投資增速將低于總體增速,拉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將轉移到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方面。
近年來通過“營改增”、個稅起征點調整、為中小微企業降稅讓利等,稅收制度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我國稅收制度對平抑一次分配差距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根據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2018年的“中國稅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應”課題研究,當前我國稅收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甚微。盡管近年來間接稅比重持續下降,直接稅占比不斷上升,但到2015年,間接稅比重仍占60%左右,直接稅比重占40%左右,其余為財產稅與其他稅種。與發達國家相比,2012年美國直接稅占比為82.2%,日本為81.3%,法國為69.6%,英國為66.7%,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為56.8%。2015年美國個人所得稅比重為40.8%,英國為27.9%,法國為18.9%,OECD國家平均為24%。雖然我國個人所得稅占比近年有所提升,但2019年仍只有6.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新興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
就縮小貧富差距來說,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其他間接稅為累退性稅收,個人所得稅為累進性稅收,企業所得稅和財產稅目前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不明顯。2013年,全國平均有效稅率為20.57%,其中的累退性稅收占比72.05%,累進性最高的個人所得稅僅占比1.2%。整體稅制結構的累退性擴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使基尼系數提高了3.1個百分點。
二、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其中就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為此,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要使“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國內經濟循環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
一是建議進一步完善勞動力需求方和勞動力供給方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同時參照市場工資水平,合理調整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報酬。“十四五”時期,必須堅持多勞多得原則,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從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分配差距。進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生產經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包括勞動報酬增長機制和薪酬支付保障機制。
二是建議構建發揮各類生產要素活力的分配體制,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讓資本、管理、技術以及數據等要素在生產經營中更加活躍起來,使企業家、職業經理人、科研技術人員和職業技能人員的各種創新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并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三是建議在全面脫貧的基礎上適當提高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確保低收入者家庭子女的義務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權益,暢通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上升通道,最大限度避免低收入群體階層固化。
第二,打破城鄉行政分割,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一是建議暢通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的渠道。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是打破勞動力市場行政性分割,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合理自由流動。2020年出臺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促進要素自由有序流動,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進一步推動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針對當前勞動力要素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意見》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暢通落戶渠道,包括“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等。真正落實上述政策措施,將大大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居民消費能力、促進國內大循環具有積極作用。
二是建議增加農民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土地要素的城鄉二元分割至今仍嚴重制約了農民工和農民的總體收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需要進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鄉行政分割局面,將附著在宅基地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巨大潛在財富轉化為農民工和農民可以平等交易的財產權益。
三是建議優化個體從業者就業環境。根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融研究院最近的一項調查,我國個體經營戶有9976.5萬戶,從業人員達2.3億人,比官方統計高出54.8%。受疫情影響,這部分人員就業受到重挫。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應當盡量挖掘潛力,為他們就業創造條件,而不是以市容優先的原則,用各種辦法“一刀切”地從一線城市擠出。就業優先與整頓市容并非水火不容,處理得當,琳瑯滿目的個體工商戶反而可以為大城市雍容華貴的市容增添幾道美麗別致的風景線。
第三,以提高公平性為方向,深化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一是建議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方向。基本社會保障屬于基本公共服務范疇,逐步實現均等化是“十四五”及今后改革的方向。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創造了高速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逐步積累了許多問題,其中十分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及今后一個時期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強調并提高其公平性、共濟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實現共享發展。
二是建議加快實施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平衡各地畸輕畸重的養老保險負擔和待遇水平,促進全國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劃轉國有資本補充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工作,應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基礎上開展。
三是建議視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調整并縮小城鄉之間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基本社會保障待遇差別。針對當前主張提高個人賬戶占比的觀點,需要強調指出,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改革作為基本社會保障最重大的項目,其方向應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提高其公平性和共濟性。目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通過連續多年調整費率并提高發放標準,統籌賬戶占比下降,個人賬戶記賬利率由2%3%上調至6%以上,已經帶來了再分配效應下降,如再提高個人賬戶占比,必然進一步擴大一次分配差距。
此外,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緊密相關的養老、醫療以及教育等民生公共服務投資應進一步加大,并與高新科技的應用結合起來(如老年康養的大數據分析、遠程醫療診斷、互聯網教育等),合理納入新基建的大盤子。
第四,提高直接稅比重,發揮稅收平抑貧富差距的作用。
一是建議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同時“十四五”時期不宜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擴大綜合征收范圍,實行家庭申報制度,并適當降低勞務所得最高邊際稅率,加大對短期資本利得、財產交易所得的調節力度。實行累進性稅率制的個人所得稅。我國個人所得稅幾經提高起征點,雖然減輕了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對促進消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一措施也使目前個人所得稅覆蓋面過窄、收入規模過小、占比過低,嚴重限制了其收入分配正向調節作用的發揮。
二是建議“十四五”時期應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科技,盡快摸清居民住房實際情況,在總結一些城市探索房地產稅經驗的基礎上,穩妥啟動開征房地產稅。目前國內房價過高,居民房貸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擠占了居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購房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003年的7.3%上升為2019年的26.7%。房地產稅的主要征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制。
三是建議“十四五”期間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遺產稅是世界各國調節財富差距的常用手段(各國開征遺產稅的時間分別為:荷蘭1598年、英國1694年、法國1703年、美國1788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國1906年)。我國已出現數量龐大的擁有巨額資產的家庭(根據瑞士銀行和普華永道的一項統計,截至2017年,我國共有373名億萬富翁,總資產達1.12萬億美元),已具備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