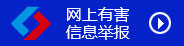改革,依然是85歲的高尚全教授的興奮點。一講起這個,在他平和的面容下,就會有掩飾不住的光彩。
2012年,在高尚全從事經濟工作60周年時,前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曾對他有一個評價,叫“有膽有識的改革者”。
他擔任過八年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參與了中國最重要三個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起草,并努力使其有更多的突破。而在第四個《決定》——即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出臺前,他又給中央提兩次建議,均指向改革的核心議題。在每一次改革的重大關口,他都沒有缺席。
如今,他每天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辦公室上班,寫文章和研討會上的發言依舊犀利,對當下的改革也有一套系統的思考。
“推進改革,如果單純從物質層面推進,必然事倍功半”
記 者:中國現在的改革,給人的感覺是頭緒很多,但效果上總不能讓人眼前一亮。你覺得這是為什么?
高尚全:中國的改革,全體社會成員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進程已經基本結束。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要調整目前已經成型的利益格局,并通過對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對公權力的約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機制。
這樣的存量調整,必然會觸動一部分群體的利益。而這些能夠在過去的體制下獲得利益的群體,往往掌握了很多的社會資源,有些甚至就是主導、執行改革措施的公權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門本身。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
并且,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者還有可能與保守的思想合流。既得利益者利用落后的思想來維護其利益的政治正當性,保守的思想則利用既得利益者的權勢,來彌補自身在邏輯上的缺陷和理論上的虛弱。
這種結合的威脅在于,在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會在落實各項改革措施的過程中采取消極態度,從而使這些改革在各種陽奉陰違中無法得到真正的落實。
記 者:有人說,中國現在的改革環境,似乎比30年前還要復雜。
高尚全: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當然比改革剛剛起步的上世紀80年代要好很多,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也已經確定,就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就改革本身而言,當前的改革難度一點都不比上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難度低。因為彼時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礙,只要能夠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識,改革就能夠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為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收益,進而印證改革思路的正確性,進一步取得改革的共識。當時既得利益格局還沒有形成。
當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思想阻力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經成為阻撓改革前進的最大障礙。
記 者:有沒有解決的路徑?
高尚全: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改革,如果單純從物質層面推進,必然事倍功半。只有從思想轉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獲得更大的助力。這既是歷史的經驗,也是現實的選擇。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綁架,那改革就必然顧左右而言他。
不少學者談及改革時,將既得利益者與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認定其為改革的阻力。實際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譬如毛澤東是富農家庭出身,周恩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曾經是舊軍閥。思想的轉型促使他們從既得利益者變成了革命家。
一些事實已經表明,當下許多社會精英乃至體制內的一些官員,已經認識到現有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并且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推動改革的前進。這些人將會是改革的有力推動者。
習近平總書記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向全會說明時指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思想是首要的。一些思想觀念的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
思想轉型的必要性還在于,改革進入到深水區后,改革的對象已經從能夠直接影響社會財富生產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問題,推進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這更間接但影響更深遠。一方面,這個層次的改革與意識形態問題更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難度與敏感度更高;另一方面,改革已經不能通過立竿見影地創造社會財富證明自身的正確性,只能通過清晰的邏輯、卓越的遠見以及總結歷史的規律來探尋要走的改革路線,并通過實踐的積累來驗證。我認為建設“思想中國”和“法制中國”是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條件和途徑。
思想轉型有賴于一個寬松的輿論環境。因為言論是思想的載體,言論沒有自由的空間,思想就難以實現真正的轉型。
“破除行政壟斷,沒有一點勇氣和膽量是搞不成的”
記 者:除了觀念與既得利益,改革的另一個難題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伴隨著中國的歷次重大改革。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就看政府給市場放權的效果。這一屆政府又提出了簡政放權。這個“權”為什么這么難“放”?
高尚全:從30多年改革的歷程看,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與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而這個轉型的核心,就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價格關系扭曲、結構調整不到位、資源消耗成本過高等問題,都與行政性壟斷范圍過寬、程度過深,從而導致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有直接的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的問題還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希望手里權大一點,錢多一點,這樣它好指揮,所以阻力還是在這里。
要減少行政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破除行政壟斷,沒有一點勇氣和膽量是搞不成的。因為推動法治、約束公權,往往會招來“左”的勢力的攻擊,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
記 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全盤布局。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并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截至目前,你覺得改革推進的效果怎么樣?
高尚全:去年5月初,我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一是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二是建議中央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三是考慮到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必須有相應的高層協調機制,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些建議都被采納了。
現在,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成立了6個專項小組,人員配置都是很強。
中央深改小組正在全面開展工作,首先把中央決定的60條、335項改革任務都分解落實到各個部門,中央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就可以把中央決定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記 者:你覺得,當前的改革如果抓幾個重點的話,哪幾個領域比較重要?
高尚全:現在的重點還是經濟領域的改革。中央提出來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不是口號,要落實,怎么落實?
譬如財政。我查了一下,2013年中國的政府基金達到了5.2萬億元,這不是個小數。怎么分配這個錢?有一個實例很能說明問題。廣東省在十二五期間要拿出100億元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按傳統的體制是由財政廳來分,怎么分?就是撒胡椒面,關系好的,嗓門大的,就給得多一些。這是政府配置資源,不是市場配置。
我向當時的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建議,將財政補貼變為股權投資,引入專業化基金管理公司,政府拿出啟動基金,吸引社會資本,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廣東省采納了我的建議,財政先拿出5億元成立一個中科白云產業創投基金,吸引了20億社會資本。這個25億,不是有去無回、撒胡椒面撒掉了,而是要投到最有效率的項目上去。
這些項目見效以后,尋求上市,政府就可以把資金撤回來,再去投入新的領域,這樣就實現良性循環了。
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呢?總的說,政府應從創造財富的主體,轉化為創造環境的主體。
3月26日,《人民日報》理論版發了我一篇文章,講的是市場配置資源。我講了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是特殊。首先一般要掌握好,借鑒好,在借鑒時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這樣才能處理好一般和特殊的關系。
市場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人類經過長期實踐總結得出規律,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更不能好處都給資本主義。民以食為天,這是個一般規律,就像餓了就要吃飯,至于你吃什么飯,外國人吃面包,武漢人吃熱干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各國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不能否定一般,就是不管你吃什么,餓了一定要吃飯,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般規律。